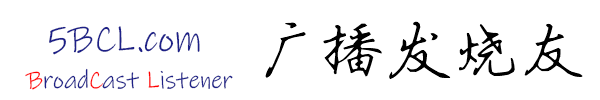每当大家都入睡,夜色也泛出倦意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我的收音机……
这又是一段回忆,人不能总是在回忆里面自我陶醉抑或是自我麻醉,但我喜欢这样回忆的感觉,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回忆。
这又是一个夏天,夏天的回忆总是伴随着从嘴角幸福地流出的西瓜汁,抬起衣袖抹一抹,幸福地微笑。对夏天的回忆,我们也许都一样,天总是很闷热,我们都享受着暑假的快乐。夏天结束,先花上几天赶做暑假作业,然后我们就又长大了。于是每过一个夏天,我们都增添了一份成熟。
这又是一年高考,四年前的这一天,我已经淡忘了。关于这些夏天的回忆,伴着沙沙的杂音从记忆的小仓库里被翻了出来,有点失真,有点模糊,像是从收音机电台里传来的懒散歌声。
我与我的收音机的回忆,就是我与我的过去的回忆。近日闲来修好了我的收音机,重新开始听了听,也像是修好了我的一些回忆。
<开往童年的火车>
我第一次听到电台广播是从床头那个老录放机上那个调频收音机听到的。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人睡了,总是在半夜突然因为各种小小的烦恼睡不着时,使劲按开那个大黑盒子的开关。广播音质特别的差,能收听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楚天音乐台。好像还有一个叫楚天儿童电台的东西,整天在广播里做广告,卖一个叫儿童收音机的东西,于是抵制不了诱惑,整天闹着父母买一部。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闭塞的小城市人都还都是很穷,去趟就近的大城市武汉还是挺难的。我在纠缠了多少个月、挨打多少次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儿童收音机”作为生日礼物——或者是其它礼物吧,谁知道呢,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早就被当前的时代浪潮给冲刷得所剩无几了,惟有小橘灯一样的温馨尚存。
儿童收音机其实挺大,像一个火车头,也像个小房子,其实我也忘记像什么了。写下这里的文字时我感觉它更像一个可爱的小火车。按下鼻子就可以播放广播,能听到湖北的很多音乐台。有一段时间我就抱着这可爱的小机器睡觉。听听流行歌曲,小虎队、草蜢、郭富城等四大天王,也有一些当时听起来特别脸红的情感故事,某某爱上了某某,写信给电台让播音员来帮忙大胆地表白。听这些时,我还羞涩地调小音量,一只耳朵贴着喇叭,另一只耳朵竖起来紧密地监听房间外的动静。由于太过于爱惜,竟然还用酒精清洗外壳,结果被擦花了一大片。尽管如此,我依然敝帚自珍。
不知道是不是儿童时代的爱好原因,养成了我以后喜欢沉迷在自己世界的习惯。但确实,那个时候,离开了小伙伴和玩具枪,我能欣然地拥有一个自娱自乐的世界,成为了一个在当前被视为“闷骚”的小众群体的一部分,呵呵。后来我上初中了,这个小火车收音机让我觉得幼稚了,被我冷落在抽屉里了。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我宁可相信是它自己离开了。
在一片漆黑中,回忆起这段时光,终究不会再回来了。我不再沉迷与倾听别人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就是故事的主角。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往事只好挑出一些谈笑于博客之间。
<海的那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对话:
孙子说:“爷爷,山的那边是什么?”
爷爷说:“孩子啊,山的那边还是山……”
孙子说:“那山的那边呢?”
爷爷说:“山的那边啊,是海……”
如果就在这里打住了,那应该是一个手机广告的对话。没想到后面还有半截。这鬼孙子又发问了:“爷爷,那海的那边呢?海的那边是什么”。爷爷很深沉地抛出一个ZY民主的话题:“孙子!海的那边,是美国啊!”
这时候,背景音乐轰轰烈烈地响起,旁白开始激动地说:“美国!一个ZY民主的国家……”
以前有拿收音机悄悄收听过敌特台“美国之音”的人,估计都听到过这段话吧,虽然原话不一样,但是意思差不多。
孙子啊,去美国吧。没想到我还有一段时间和那乖孙子一样想去美国。是无条件地想。那时候我在上初中,班里一个好朋友的亲戚去过美国,带来一些所谓的ZY思想。该朋友向我披露了收听“敌特电台”的方法。当时我震惊了。我印象中需要用无比专业的器材才能收听的东西竟然用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就可以听到。于是我疯狂地攒钱,等到有一百多块的时候,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台德生R909收音机。这个小盒子让我爱不释手,随我一走就是七年。
于是这后来,多少个夜里,我窝在被子里把天线拉得长长的,听听那时以为的“ZY民主”思想,并深深地为之陶醉,从此立志一定要去那个美丽的ZY国度。除了听美国之音,还不停地拨动飞轮看看还有没有从世界那边漂过来的声音,因此也断断续续收到过法国的电台、梵蒂冈的宗教广播、日本的哇里瓦拉听不懂台。后来还收到了一些不停地播报“8241,3956,2323,5266,……”这样的怪异密码广播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在干啥,权当是在搞间谍活动吧。
幼稚的心灵是很纯洁的,自己就不会容许污染的进入。但幼稚却又自认为成熟的心灵是很可怕的,简单的说,会学坏。今天来笑话以前的无知,也是很无知的。谁知道呢,人的思想总是在不停改变的,今天你想到的,今天你看到的,今天你认为必然的,在将来的一天也许都会崩溃掉。唯一不变的是聆听与诉说。
还是要感谢美国之音这个国际大骗子,让我知道了怎么收听短波电台,至少让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窗口。当我将天线对准点点星空,我在想,这淹没在沙沙杂音中时隐时现的声音,竟然是来自地球的某个角落。在那个角落有生死、有爱、有正义与邪恶,有笑。而我却看不到他们,他们在哪里?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了。想唯心地问一句,他们真的在那里吗?只有黑色的星空安静地看着我,夜色已经很深了。
短波让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却让我们的感觉变遥远了。
夏天又到了,北方的夏天和我的家里很是不一样。在家里,夏天夜里最大的奢望就是让自己赶快睡着早早到天亮。每天夜里先用温水洗去浑身疲惫,然后像涂防晒霜一样将花露水涂满全身,再摇着扇子在凉席上忍受热空气的煎熬。后来家里添了电扇,添了空调,但是我还是老觉得热。没办法,胖子怕热,呵呵。
在北方要好得多,虽然白天的温度还是那么热,但到了夜晚却不那么闷了。南方的热惹得虫子在夜里吱吱狂叫,窗外往往一片悉悉索索声;而现在在我的窗外,除了学校的大杜鹃时不时寂寞地叫几声“光棍真苦”外,就只剩下风擦过枝头的留声了。
上次写了点关于自己和收音机的故事,其实算是很牵强了。收音机是什么?其实是承担了我们青春的一个载体。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没有五颜六色的互联网,没有便携的PSP,没有时尚潮人手中的IPOD。我们真正骄傲地拥有的只有一台或者是地摊上买来的、家里落灰的或者是自己拼装的收音机。客观地想想,其实这么多年来,广播里面的咿咿呀呀一直都没变,可是主持旧貌换新颜了——不对,是旧声换新音了。听惯了原来那些声音的我们,总是不住地想,电波里原来的他/她哪里去了,以前那个刚跨出校门的他/她是不是已经有了孩子,曾今那个坚定成熟的他/她是否已经头发发白,或者电波里几年前那个苍老的声音是否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开始诉说。对收音机时代的缅怀,也是对我们青葱岁月的依依不舍。
今天周二,广播停台没得听了。欧洲杯如火如荼。闹中取静,接着写点东西自娱自乐。
<心中的DJ>
说来好笑。我内心里一直觉得我是一个DJ。
我上高中了,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的高中过得很是莫名其妙。
在常理上,高中的生活是单调得要呕吐的,而我却跟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化学老师开始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学习。那时候我们高中的学科竞赛刚刚开始兴起,学校想在国际上拿一两块竞赛的金牌。对化学很有热情的我去老师那里毛遂自荐了。我当时一心想去中科大学化学,希望做一个有热情的戴着厚厚眼镜的科学家,去国外的高等学府和研究院做最前沿的化学研究。由于我对化学有那么一点点的天赋,加上阅读了很多当时看来超乎高中生理解能力的化学书籍。我成为了学校为化学竞赛培育的一个“苗子”。
简单的一次选择,我在高中的前两年就这样荒废进去了。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投入到无穷无尽反反复复的化学学习中。各种大学化学专业课课本被我反复翻阅,各种大学化学实验都在我手上练到烂熟,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喝水都用烧杯。我也参加了在武汉大学的集训。学校的领导一次次地看望我们几人,勉励我们,祝福我们。何等的光荣啊!
刚枪在手,重任在肩,这样其实是可怕的。当浑身光环退去,我却不挂一丝荣誉地怔在了那里。这段为校争光的经历突然就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可耻地失败了。人群将我捧得很高,却又突然四散而逃,去追逐他们新的希望之星。原本舞台的最亮点在一瞬间就变成了孤独的角落。
那个时候我依然爱听收音机。广播里信号最清楚的是我们本地的孝感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是一个年轻的声音,他说他叫江枫,江枫渔火对愁眠。江枫是很温柔的小男生型的,在电台里说话总是很缓慢。但是他又很有个性,甚至在广播里失态地斥责怒骂一个背叛了自己的朋友。他喜欢放一些很另类很缓慢的歌,北欧的、加拿大的、台北街头的、北京地铁过道里的,统统都是他的最爱,这些很凑巧也都是我的最爱。我的书架上,一小排CD碟也许和他那里拥有的几乎一样。
江枫他说他是个很自我的人,不愿意见他的听众,希望能保持自己的一个小小角落。而那时的我已经将自己蜷缩起来,藏起自己原来的那些锋芒。在学校里,我喜欢挑出那些最能扣动我心弦的歌曲,放给大家听,我热切地期盼我埋头用功的同学们抬头给我一个肯定的微笑,终于,有人告诉我:“你放的歌,很好听,很有味道。”我享受这个被肯定的感觉,我相信音乐能让心沉醉,他们肯定了我的感受,让我有些高兴。
高三我努力的学习,使劲赶上完全没有学过的两年的知识。原来对化学的热情已经变成厌恶,关于人生不公平的痛苦已经在我身上萌芽,我不确定它们会不会将苦涩的根扎得更深。每天晚上仍然听江枫的节目,听他放小红莓乐队,空灵地让人有归隐的感觉。终于我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不想考大学了,我想成为一个DJ。我不会和其他DJ一样去吸食毒品让自己兴奋,我会很冷静,我想让那些欢乐的人在我缓慢的音乐下沉思,找到他们自己真实的一面。音乐是最好的迷幻剂。
在节目中宣称从来不给他的听众写信的江枫,给我亲笔回信了。黑色墨水,普通信纸,有些别扭的字。他告诉我,其实他从来就没有想过选择做一个DJ,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从大专院校中文系毕业的乖孩子,他的梦想远不是在电台做一个在半夜直播的DJ。可命运的咽喉需要用自己的实力来扼住。他说他感到自己的卑微,如果我能考大学,走一条能确定自己命运的路,他会感到欣慰。
我收起了收音机,开始了疯狂的学习。200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快结束时的某一天夜里,我一个人踏上了北上求学的列车。
我打开我为大学时代新买的收音机,到了熟悉的时间,江枫主持的节目却已经不复存在。而我心里的DJ还在放着离别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