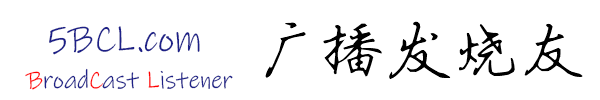冬夜
(一)
年近三十,依然书剑飘零,不知何所当行,何所当止,不知何处是家。
冬天的傍晚。在一个北方的小镇,一条寂静的街上,我走进了一家第一眼看到的小饭店。
见有人来,正在听收音机的主人站起来迎接。是个 40 左右岁的男人,高高的个头,黑黑的脸膛,像个北方汉子。我感到一双有力的手立刻就卸去了我背包的重负。接着,是一条白毛巾在桌上擦。那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礼貌。
“冷吧?”端过来一把茶壶和一只玻璃杯。倒水时冒出的热汽让我闻到了一股北方人爱喝的茉莉花茶香。
“还行,不算冷。”我一边回答,一边打量这只有两张桌子的小房间:整齐、干净。
“吃点什么?”主人低声询问,眼睛静静地看着我,没有像大城市常见的那种过份的殷勤。
“有新鲜蔬菜吗?”
“冬天,新鲜蔬菜少……只有尖椒,能吃辣的不?还有花生米……”
“那就油闷尖椒和花生米。”
“好的,马上来。”没有多余的话,转身进了后面的厨房。
收音机音量已经被关小,所以能听见刀、勺磕碰和点火的声音。不一会儿,菜就端上来了。两盘小菜,二两小烧,两个烧饼,外加一壶茶,这是我一天中最正式的饮食。主人的热情和手艺完全表现在这一份饭菜之中,我内心不禁生出一阵感激。
主人仍坐回到原来的地方。他指了指收音机:“听收音机不?”
“不,您听吧。”收音机的声音大了一点。那是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我的到来,他中断了有十多分钟。袁阔成的评书的确不错。可是这三国演义,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我本想向主人借收音机,找找是否有“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那样的歌。一想,未必能找到,算了吧。还是专心喝酒吧。
两杯酒下肚,身上开始热起来。这温暖的小屋,让人坐下就不想走。可是,我得走了,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得去找旅店。
我起身掏钱包:“多少钱?”
“给八块钱吧。”仍然没有多余的话。
我对这个价格心生疑惑。即使是小地方,未免也太便宜了点。我没找到零钱,拿了一张拾元票给他。他略一迟疑。我立刻反应过来:“不用找了。”说着背上背包。
“那不好。我出去破开。”就要戴帽子出去。
“不用了,没关系的。”我抢先跨到门边。正要推门,又停住了:“请问,附近有旅馆吗?”
“有哇,往前走 100 米。”
“谢谢!”我推门出来,他送到门口。在他关门的一瞬间,我看见了一双眼睛中流露出的善良的祝福。
(二)
天色已黑。幸而两旁的店铺门口都有灯光。走不到 100 米,果然看见一块小招牌:“春晖旅社”。我推门而入。寒风随我一起挤进门来,形成一股白色的烟雾。透过白雾,一个女人已经迎在我面前。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略带修饰的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成熟和淡雅。在她习惯地用手拢着卷发时,仿佛有一股淡淡的香气从她的指缝间流淌出来。
“来了?”嗓音甜美、纯净。是“来了”而不是“您好”。那种大城市的廉价的“您好”我听够了。我喜欢听“来了”、“吃了吗”这样的问候。
我不知如何回应这问候,只管卸身上的背包。她上来帮我。她拨开我笨拙的手,只一下,就代替了我一系列繁难的动作。在手和手接触的一刹那,虽然感觉不到温暖,柔软之类,却能体验到热情。大城市的热情常常表现在语言上,而小城镇的热情表现在行动中。
“有空房间吗?”我问。其实我已经无需问。我已经感觉到了。
“有。有多人的大房间,也有单人的小房间。大房间便宜,也没人,但是冷。今晚不会有人来了,我看你就住小房间,按大房间付费好了。你住几天哪?”这么一长串介绍,不容你打断。
“只住一晚。”
“那就更简单了。”说着,领我去所说的小房间。
一桌、一椅,洁白的床单和窗帘,一盏紫红色的台灯弯在桌角;一双墨绿色的拖鞋摆在床头。我换鞋间,她又提来一壶热水和一个脸盆:“你就在这屋里洗洗吧,别去盥洗室了,冷。”
“好的。”我无言。连“请您休息吧,我自己来”这样的话都不会说。
当我洗去了一天的疲惫,舒服地躺倒床上的时候,她又来敲门了。轻轻的“得,得”两声。我不便穿着内衣去开门,喊:“请进!”因为我知道她手中有房门的钥匙。
“连个电视也没有,真不好意思。借你个收音机解解闷吧。”随手把一台黑色的小收音机放在我头边的桌上,转身,轻轻地带上门出去了。背影消失处,只留下一缕淡淡的幽香。
我打开收音机,略作搜寻,找出一个电台,正在播徐小凤的一首老歌:“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的《无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古至今就众说纷纭。今天我当然也弄不明白。只是徐小凤的歌的确好听。深沉,有韵致,不像很多歌星那么张扬。不过,我真的累了,胡思乱想着就睡过去了。
忽然,我感到有一只手在抚摸我的脸。从头发到耳朵,到嘴唇。像母亲。我半睁开眼,看到的却是她,不是在摸我的脸,而是在给我掖被角,闭收音机。婀娜的身影在她关断台灯的同时,突然消失了,随着轻轻的一声门响,只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
我静听四周,四周悄无声息。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寒冷的冬夜,在这小小的旅店里,只有我们二人。刚才我愚蠢地睡着了,她在为我守夜。现在我们都没睡。
早晨,一线冬天的阳光照亮窗帘。我该走了。她送我出门。在关门的一刹间,我又看见了一声无言的祝福。
走出十几步,我回头再看那块小小的招牌:“春晖旅社”。我拉了拉背包带,那上面有她的体温和幽香。走吧!严冬就要过去,春晖就在前面,我想。
(2004-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