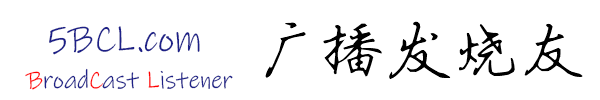日本孩和收音机的故事
(一)
小顺子大名叫赵常顺。
他家和我家是邻居,所以,我们从小是玩伴,长大是同学。他个头不高,却很机灵,学习也好,大家都爱跟他玩。我就更不用说了,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放学后,我就上他家,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收音机。他爸妈从来也不限制我们,只是嘱咐我们别老乱拧,小心拧坏了。那是一台老式的日本造收音机。黑黄的机壳,右侧上部镶着一块方玻璃,里面有一个像表针那样的指针,一拧下面的旋钮,指针就跟着转,就能调台了。后来,我们还一起装矿石收音机,玩疯了。
可是,慢慢听说,小顺子不是他爸、妈亲生的,是拣来的日本孩儿。“小日本”这个外号也在同学中间偷偷传开了。我呢,不管这些,还是和他好。
应该是在1963年。有一天,他悄悄跟我说:
“我要回日本了。”
“你真是日本孩儿?”
他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二)
那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
清晨4点,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中学的数学教官赵景生先生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爬起来开门去看,只见晨曦中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右手抱着一个长布包,左手还拎着一个方布包,用痛苦和疲惫的眼睛望着他。来人认识,是他国高的同事,物理教官,日本人,名叫渡边宏健。名为同事,实则中日教官之间互存芥蒂,并没有往来。他这时候来找我干什么?赵先生怀疑地打量着渡边宏健,不知说什么。
“能让我进去说吗?”渡边先生操着生硬的汉语、明显带着乞求的口吻。
“请吧。”赵先生只好叫他进屋。
静默了几秒钟,渡边先生终于说话了:
“赵先生,你知道我们日本人现在的处境……苏联占领军今天就要把我们遣送了,可是……可是……我夫人病着,路上说不定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实在是没办法……您能不能……这孩子……”说着,打开了怀里的包裹,露出一个婴儿的小脸。孩子正睡着,粉红色的小脸上湿湿的,不知是汗,还是泪。
“我想请您照看一下这孩子,以后我会想办法来接他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赵先生,拜托了!”
赵夫人已经醒了,不等丈夫说话,先接过了孩子。她很喜欢孩子,因为结婚五年,她还没有生育。
赵先生凝视着渡边先生的脸。这张脸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赵先生想,你们也有今天,真是天照应。可是,如今这个可怜的人是在为了一个孩子在乞求,孩子并没有罪。他只能接受。中国人是善良的。
“我答应你!”
渡边先生闻声,紧张的精神稍稍松弛了一些。他拿起那个方包袱,放在桌上,打开来,原来是一台收音机。前两天刚刚用它收听过天皇投降诏书,布满灰尘的外壳也许还混杂着他的泪痕。
“没有东西送给你们,这收音机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再见赵先生,拜托了!”说完,向赵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出门去了。
(三)
小顺子说,这一切都是他爸爸不久前亲口告诉他的,他不能不相信。他还说,先是公安局来找他爸爸,说有一个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寻亲,落实到我们这里。那天,公安局来了两个人,问他爸爸,是否有一台日本老式收音机?爸爸说有,随即拿来给他们看。公安局的人当着他爸爸的面打开后盖,把底盘抽出来。在铁皮底盘的贴面板的一侧,发现了用尖头工具刻成的四个汉字“渡边一郎”。公安局人说,这就是要找的那个日本孩子的日本名字。这孩子的日本父亲很有心计:他料想贫穷的中国人不会轻易丢掉一台收音机,所以把他孩子的名字刻在底盘上,以便日后相认。现在果然证实了,小顺子就是那个日本孩儿。而且,他的日本父亲正准备把它接回国去。
小顺子不愿意去日本,更不愿意离开养父母。
但是养父母却同意了。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亲自为他办好了一切出国的手续。他说,当时有很多逃难的日本人半夜里偷偷把孩子扔在人家门口就走了。可是我们不同。渡边先生是当面把孩子交在他手上,并且说日后一定想办法来接。他是拜托我照顾,并没有把孩子送给我们,而我们是当面答应过的。中国人要守信用。
而母亲却一连哭了几夜。
就这样,小顺子于1963年的一个夏日踏上了归国之路。那年他18岁,高中三年级毕业。因此我也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四)
接下来是10年文革。赵先生没有躲过那一劫。他因为当过国高的教官,被定为日本特务、历史反革命,押在大狱里。他的苦命的夫人就此一命呜呼。赵先生倒是活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然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苍老、孤独的世外人: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在街上碰上他,尽管岁月沧桑,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我上前叫了一声:“大爷!”他凝神看了我半天,摇了摇头,仍旧一拐一拐地走他的路去了。他是认不出我了,还是不愿意拾起痛苦的回忆?
我是个收音机爱好者。有一次,我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他老人家曾经有过一台日本老式的收音机,这正是我多年渴望收藏的品种。不知那收音机还在不在了。要是还在,我能买下,不仅可以向同好们炫耀一番,也是对我儿时生活的最好纪念。然而,我立刻感到一种羞愧。对这样一个老人,我竟产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未免有点太残酷了吧。
(五)
1983年的一个夏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陌生:
“您是×××先生吗?”
“是。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赵常顺。”
“谁?”
“赵常顺。×××!我是小顺子呀!听清了吗?我是小顺子!”
我拿着话筒的手待在半空不动了足有半分钟。
他终于回来了。他是接到他养父病危的消息回来的。此前,他多次来信、来电找他的养父,总是没有回音。他以为养父已经死了。这次,他突然接到养父托人打来的电话,希望他如果可能,就回来一趟,自己怕活不长了,想见他一面。
他接到电话,立即办理手续,星夜启程。当他见到他日夜思念的中国爸爸的时候,爸爸已经躺在医院里。他服侍汤药,寸步不离。老人临死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用他鸡爪一样的枯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他儿子的脸,那张分别时泛着红光,如今已满是胡楂的脸。
(六)
小顺子是通过老邻居辗转打听到我的电话的。我立刻把消息告诉了我们的老同学。几天以后,大家在一起聚会了一次。一是见见国外回来的老同学,二是恰当毕业20年的纪念。
聚会办的很热闹。有畅叙悲欢离合、同学情谊的座谈,有推杯换盏、慷慨悲歌的畅饮,也有焕发青春,各展风姿的舞会。然而在所有的过程中,小顺子始终沉默寡言,不唱歌,也不跳舞,只偶尔和我说几句简单的话。大家理解他此时的心情,没有过多的打扰他。
一个月以后,养父终于死去了。他眼含泪水,忙着办理后事。但是他不懂中国的事情,里里外外,都是我帮他办。他总是很客气地一次又一次表示感谢,除此,再也不多说什么。
(七)
办完了后事的第二天晚上,他给我来电话,邀我到一个饭店去见面。我去了。
坐定以后,他仍然沉默着,只是不住地让我吃菜、喝酒。他自己也喝。开始还喝得慢,后来就渐渐快起来,一杯接一杯,像日本电影中武士喝清酒那样。
我怕他喝醉了,按住他的杯子。他挣扎着还要喝。最后,他说:
“好吧,不让喝酒,唱歌行吧?”
“唱歌行。你唱一个日本歌我听吧。”
“唱什么呢……就唱你们熟悉的北国之春吧!”
说罢,歌声已经低低地传了过来。他的男低音很有磁性:
“…………(歌词是日文,请原谅作者不会写)”
那充满诗意的春天的旋律在小小的房间中回荡着,仿佛将所有的痛苦都化为了力量,让人向上。以往我听日本歌,感到日本歌曲中总是有那么一点哀怨的意味,一唱三叹,让人唏嘘不已。惟有“北国之春”,一扫低回哀怨的情调,代之以昂扬奋发的旋律。我想,这也许正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吧。
歌声结束了。他抬起眼睛望着我,眼珠一动不动,仿佛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之中。这是他很少有的。
我说:“你唱得太好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日本歌!”
“谢谢你的夸奖。”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垂下眼皮,平静地说: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
“明天?”
“是。”
“我去送你。”
“不必了。我谁也没告诉,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我一时无言。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弯身从旁边提起一个方布包袱,放在桌上,打开来。
“还记得这台收音机吧?”
“当然记得!”一霎时,儿时的一幕幕又在我的脑中翻开了。
“我爸爸一直珍藏着它。他说,看见这台收音机就像看见我一样。他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让我把它带回日本,把它交还给我的日本爸爸,还说让我替他谢谢我的日本爸爸,因为这台收音机曾经让他度过了那么多寂寞的日子。”
我无言地静听着,仿佛听到那个老人的低语。一个多么可敬的老人!
“我已经把一切都料理完了,我真的该走了。这期间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无法谢你,送你东西你不要,让我没办法。今天,我改变了主意,把这收音机带来了。我想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为了我们的友谊,不要推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应该留在中国!”
我无言地静听,眼泪几乎滴到桌上。
“它还能用的,让我们试一试吧。”
边说边把插头插到墙上的插销中,略微调了一下旋钮。小屋中立刻飘起了二胡独奏的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我不只几十次听过它,没想到,在这样的时刻又是它。二泉映月不愧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它的凄婉、不屈的调子让你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八)
第二天早8点半,我赶到机场。小顺子看见我,叹了一口气:
“你还是来了。”
“我代表大家来送送你。”
“谢谢大家,谢谢你!”
我打开提包,掏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
“我想也给你留个纪念。”
我把盒子递给他,他双手接过贴在胸前。
“这是中国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虽然中国的电器水平远不如日本,但是,我希望你用中国的收音机听中国,听汉语。”
他突然退后两步,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我深深地弯下腰去:
“记住了!谢谢,谢谢!”
检票了。他最后握了一下我的手:
“洒羊那啦!再见!”
我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走进了机舱。我感到,这几天的时间学到的东西,比我一生学到的都多。
( 全文完)
(挽断作于2004-06-26,首发德劲公司网站“收音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