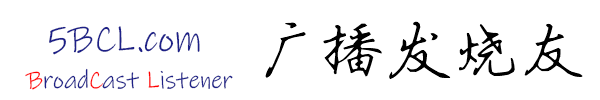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电视还不普及,人们只能用收音机听点东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傍晚时候的收音机,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让生活充满色彩。要是没有傍晚的收银机,生活得多么单调无聊!

那时候,我非常迷恋收音机。其实,小时候就听过收音机,只是听不懂,也没耐心。那时候,在姥姥家玩,到了中午或傍晚的时候,姥姥拉一下炕头的绳子,那绳子像是灯绳,却完全不能控制灯泡,只能控制炕头上面墙上的小红喇叭。绳子是开关,只要拉一下,就等于打开了炕头的小红喇叭,能听到里面的样板戏,还有村干部的讲话。姥姥不识字,却会唱整段的《沙家浜》、《红灯记》。那时候,我娘还留着大辫子,就像是铁梅,不过,已经生了姐姐和我,就算是不能干活的铁梅了。
后来,小红喇叭撤掉了。姥爷买了一些戏匣子,用黑色的皮子包着,到了傍晚就要听评书,听相声。收音机里总是播放新闻,姥爷不喜欢听,就喜欢听评书,要是没有评书,听一段相声也是可以对付一下的。我在姥姥家玩,跟着姥爷听评书,听相声。时间久了,就觉得傍晚一定要有点娱乐节目,即便没有娱乐节目,也要自己找点娱乐节目。
白天辛苦,傍晚就应该休息了。到了傍晚,倦鸟归林,牛羊回圈,人也应该回到家里,听听收音机,算是娱乐一下吧。只是,那时候节目比较贫乏,必须等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听到评书,听到相声。而夏天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天还亮着,却早错过了评书的播出时间,听不到了,只能忍受晚七点的新闻。到了七点半,可以听上十分钟的广告,再听二十分钟的相声。虽然那时候的相声也不多,经常出现一段相声反复播出的情况,但我还是要每天认真听,乐此不疲。
夏天的傍晚,蚊子比较多。鸡们不怕,早就跑到鸡圈里去了,后来竟然趁着放风的时候飞到了树上,毫不顾忌地拉屎,弄得树杈上、地上都是鸡屎。狗也不怕蚊子,皮毛厚实,到处乱跑。我听收音机的时候,腿上被叮了好几个大包。大黑狗卧在我脚下,摇着尾巴,用舌头舔着我的手心。娘在东屋做饭,炊烟顺着烟囱慢慢飘出来。邻居家的烟囱也冒出了炊烟,弥漫在院子上空,让人觉得有些虚幻,就像是梦境中。后来,我看电视剧《水浒传》,导演用了大量的烟雾,让我觉得似真似幻,就像人生一样不真实。

我第一台收音机是向舅舅借来的,有录音机和收音机的功能。录音机用来听英语,只是没舍得买几盘磁带,就只能听收音机了。不过,那个录音机并不好用,经常出现咔吧咔吧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不习惯的人会被吓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给娘要了十几块钱,找到舅舅,让他带我去买收音机。舅舅给我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收音机,用两节小电池。每天傍晚收听一些节目,让我有了表演的欲望。后来,扩展到每天中午听评书。评书节目从傍晚转移到了中午,让我有些欣喜若狂。在十二点半的时候,评书会准时开播。而我十二点才放学,要在放了学之后,背起书包,风风火火往家跑,才能赶上听评书。
那个时候,老师管得很严格,不允许带着收音机到学校。当然,要是我偷着带着去了,老师也发现不了,只是会被同学们偷着拿走了,就找不到了。于是,收音机只能放在家里听。当我满头大汗地跑回家里,拧开收音机,听评书的时候,屋子里有点凉快。大黑狗在我的脚下卧着,尾巴摆来摆去,弄得地面有些浮土飞起来,在窗户透过来的阳光里飞舞。屋里似乎有着上午阴凉的气息,还没有完全变得燥热,而窗外的槐树树影婆娑,透过窗户,落在炕上。要是在屋子里,整天不出去,似乎就不用感受外面的炎热了。那个时候,家里没电扇,但屋子里冬暖夏凉。屋子是土坯衬里,青砖表外的建筑,屋顶架了大腿粗的横梁,还有胳膊粗的椽棒,上面铺了苇席。我躺在炕上,听着评书,看着屋顶的椽棒,一根一根数,居然能数清楚。可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就没有那个闲心了。
傍晚,夕阳落山,余光透着血红色。鸡们飞到树上去了,被夕阳的余光镀上了一层橘红色。我拿着巴掌大的收音机,在院子里踱步。一边走一边听,忘掉了老师讲课的内容。以至于,我经常听收音机,成绩一落千丈。娘想要限制我,不让我听收音机,还给我藏了。但我总是能找到,还能拿着收音机,跑到外面去听。娘限限制不了我,就只能让我自己做主了。
收音机里的评书有磁性,会吸引着我每天按时收听,而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情节。或许,那时候正是由白天转入黑暗的时候,人们都安静下来,动物们也安静下来,阳光也渐渐没有了。这个时候,最让人悲哀。听一听收音机里的评书,会让人得到心灵的慰藉。听一两段相声也是如此,哈哈一乐,白天的不痛快就全都烟消云散了。爹喜欢脱了鞋,靠着被子,翘起二郎腿,听我的小收音机。可是,我不愿让他听,只是喜欢自己听。他听的时候,什么节目都能听,不管是不是评书和相声。就是广告,他都能听上半小时,还真的相信广告里的药,说能治病,却从来舍不得买。

我的小收音机里的电池没电的时候,收音机里的声音变得非常小。我能把收音机放到盖着水瓮的白铁板上,通过水瓮的回声,还能听上几天。要是不行了,就把电池抠出来,用牙咬,用锤子砸,把电池弄得变了形,但不至于砸破了,电量竟然恢复了不少,还能听上一段时间。
我想,到了傍晚就要听收音机,或许是姥爷给我形成的深刻印象,抑或许我自己有些文艺细胞,要寻找一些文艺方面的乐趣吧。不过,傍晚的收音机仍然让我着迷,也让我想起很多事情。似乎收音机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不是一回事,更像是一种高级的文明,而现实已经一塌糊涂,即便是现在,还是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