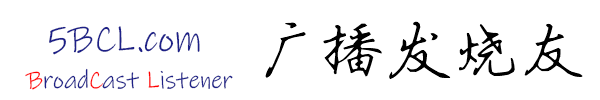作者:李文祥
我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经常外出学徒、做小买卖,闲暇时无聊便凑到热闹处听人说书、看看戏什么的,时间长了便对外界的罕闻稀事和看戏产生了兴趣。在封闭的年代,父亲的这一兴趣爱好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的奢侈品;直到晚年一个偶然机会开始接触广播,与收音机结下良缘,才算满足了他的这些爱好。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天,在我们村附近矿区上班的一个亲戚告诉父亲:说他早晨从大喇叭里听到我写的报道。父亲听后很兴奋,又不知怎么回事,为了探个究竟,就隔三岔五到矿上高音喇叭下听广播。那时我当编辑,偶尔搞一次采访,广播里很少播我写的报道。父亲在高音喇叭下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听到我的名字及报道,很失望。
这事传到我耳朵里,随即我就去买了一台砖头大的牡丹牌收音机寄回家,父亲如获至宝,用毛巾裹起来,不让任何人动。父亲那时已上年岁,觉也少,呆在家里就是听收音机;摆弄来摆弄去,对收音机里的节目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当天的栏目内容很多也能早知道。
起初,父亲主要是听戏。从中央台到省、地台和周边省的一些台,挨着听,什么样的戏曲都有兴趣,一天到晚,巴不得把收音机里播放的所有戏曲“一网打尽”。
父亲听戏很投入,总是提前找准台,播音员(主持人)话音一落,调大音量,随着戏曲旋律便进入状态:时而静静坐着,时而半躺着,眯着双眼,一脸兴奋状,尽情地享受唱腔、曲调的美感,倾心欣赏唱段的精彩内容,还时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几句。遇到他熟悉的名曲老段,更是如痴如醉,那真叫过瘾!
时隔几年,我由做编辑改当记者,新闻广播中经常有我采写的报道,父亲则改变了收听习惯,每天早早打开收音机先听新闻。一听到有署我名字的报道,顿时就兴奋起来,像得了大喜,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有的重头报道一天要重播几遍,他就反复收听几遍。那些年我写了多少报道?是什么内容?早已忘却。而父亲则全给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早晨播了我写的什么内容的报道、是谁播的,那年总共播了我多少篇报道?哪月写的多,哪月写的少;哪篇写的长,哪篇播得短,都如数家珍,清楚准确。
父亲听收音机的兴奋点、关注点和所派用场,是多方面的。一次,一位近邻要来京找我办事,车票都买好了,父亲晚间新闻里听到我发自江西的报道,就立马告知对方,过些日子再去吧,他不在北京!然而,父亲关注更多的还是那些国内外大事、有趣的新鲜事。诸如:某大学校长去世了,某地获得了粮棉好收成;白天华北有小雨,明后天要大风降温等等。转身,他还要把这些东西告诉街坊邻居和家里人,自己的心里总是亮堂堂的。给人的感觉是,他知道很多新鲜事,懂得不少新道道。
那台牡丹牌收音机块头大,耗电量大,为了省钱,父亲总是把电池耗尽炸干才肯更换。为此,我又给他买了台质量高、耗电量小的红灯牌收音机,碗口大,塑料壳,灯笼形状。父亲更是喜欢,一天到晚双手捧着,有时贴在耳朵上听;躺着或睡觉时,把它挂在炕头墙上,形影不离,一直伴随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父亲去世时,亲人们都知道他的这一爱好和这一心爱物,便将这一永不腐烂的塑料壳儿收音机放在棺材里,永远在陪伴着他!